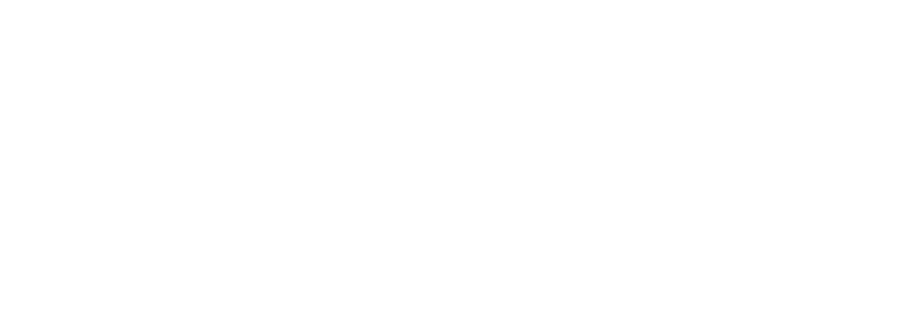缘起
主持人:
首先我们想请熊律聊一聊为什么清律会增加一个这样的专栏,其目的是?
熊定中律师:
2022年清律在人员增长比较迅速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一些对于律所一致性有所冲击的事情。
原来只有北京一个办公室的时候,其实不太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从2013年组建团队以来,大家磨合了很长时间,对彼此都相互了解了,清律的文化也是大家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缔造出来的。但是从19年开始,我们迅速地布局了全国的规划,引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大家一进来就面临一个已经有自己独特文化和风格的一个群体。这种碰撞难免会出现一些大家不希望出现的事件。
可能新加入的同事会发现,我们清律看起来跟别的律所又有一些新的不同,就是首席合伙人总批评人,而且还是公开批评,2022年已经点名好几次我们的同事了(但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乐意经常去处理的)。我注意到被批评的同事,其实在主观上并没有说故意去挑战律所的文化或者管理秩序,都是不小心踩到了某个雷。在这类事情发生几次之后,我和管理团队都在反思,到底清律还有多少雷在,好像很多人都不敢做管理动作了,因为很多被处罚的还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所以在某一次的合伙人会,大家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公开的渠道,定期让大家了解自己所在的律所到底有哪些没有写在文字里面的常识。
最终经管理侧商议定下来的模式是,由我们的律所同事就一些自己感兴趣或者不太拿得准的问题与首席合伙人进行公开交流。
这个公开交流的过程第一是让我们新人可以迅速了解这个组织的特点,第二也是要更进一步地澄清大家的误会。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环节知道你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里,更多地了解这个组织和机构,知道这个平台在做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或者说禁止做什么。
关于为什么叫“一言”,一言不是一言九鼎的意思,而是一家之言,就是这只是我的观点。但恰好我现在是首席合伙人,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我们律所的战略观点。当我不是首席的时候,可能会有新的首席去表达他个人在战略方向的观点。这个交流环节里面没有表决,也没有定论,只是一个观点的交流过程,所以这就是这个环节设定的意义。
· 律务部门的痛点。
· 清律的管理特色与氛围。
· 什么事情不符合清律的文化?
· 法无禁止皆可为?
· 清律是清律,我是我。
业务分管合伙人:
作为已经任期了5年的业务分管来讲,有个困扰我的问题想与熊律聊一聊。就是我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我们能够供给的资源,这个紧张程度一直得不到缓解。
这个需求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咱们律所的发展比较快,每年人员都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另一个方面是咱们没有除了律务部门之外的部门来承担律所的其他执行需求,包括市场、行政等。
目前这两个方面的日常基础工作完成得还可以,但是消耗了律务大量的时间,导致律务中台的信息中心及数据统计部分的职能未能发挥出来。如何将律务中台关于数据统计的价值发挥出来,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想听熊律聊一聊。
熊定中律师:
律务的问题确实是一直存在的。19年设立律务部门,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信息集中在一个部门,以及能够给其他人提供指导。
我们目前,让信息集中在一个部门这部分完成的还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就面临下一个困难,即在数据量增长的情况下,第一我们能不能正常接收这些数据,第二我们在这种困境下,怎么去分析这些数据。这些问题应该由分管合伙人来解决。
如果在日益增长的数据量下,我们没有办法腾出时间来做数据分析,那是不是可以考虑:
第一,降低采样的精度来保证我们决策的准确性。具体到底哪些精度需要降低,是业务分管需要去考虑的。
第二,除了降低收集数据的精度外,降低数据收集的宽度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用这些数据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从提供的支持倒过来看哪些数据是至关重要的,并重点去抓这些数据。
第三是我们的财务预算,我们清律的财务编制仅仅支持多少个律务是给定的,那有没有可能在精度和广度收缩的情况下,把部分工作交给行政部门。这都是需要去考虑的,甚至更极端一点,不排除我们中台部门收缩到一个极致是只做数据分析,不做基础工作了。将基础工作交回给各团队秘书。这个不确定性很大。
前两周其他所(炜衡所)的管理团队的几个合伙人过来进行交流。他们比较苦恼的是,他们新租了一层房子,今年业绩影响又很大,他们的亏空是需要高伙去承担的,他们需要拿钱去贴这个房租成本。但清律却没有这方面的苦恼。我们19年搬到清华科技园,到现在22年我们北京的人数几乎上升了一倍的情况下,房租没有上升,甚至我觉得再多一倍的人,我们也撑得下。这在管理侧意味着新加入的人带来的律所收入都是利润。这个利润有很多的去向,我们可以增加公共人员编制来提升律师福利,也可以进行分配,让我们的律师自己拿到的钱更多。
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在国内我们是第一个收入和支出脱钩的律所。其他律所的模式都是人上来收入增加,但同样成本也成比例上升。这就意味着我们清律的管理侧有非常多的管理工具可以使用。我们的管理空间非常大,因为第一你有钱的空间了,这个钱到底用来做什么?你是可以出很多政策的。你是分给大家还是提升福利,还是兼而有之,都可以去考虑的。第二他们特别羡慕我们这个办公模式,但并不是所有律所都可以适用的。目前清律的工位是不收费用的,如果下一步我发现我们的人员更多了,我们承担不了,而我们又不想提升成本的时候,我可以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其他团队。清律会有很多经济杠杆可以使用,这个政策的储备是很多律所不具备的。
所以我期待各个分管合伙人思考,你们应该考虑你手头有什么牌可以打。
业务分管合伙人:
第二个问题:大家普遍觉得清律的管理气氛比较压抑,尤其是跟熊律聊天的时候。所以熊律有没有必要跟大家做一定的澄清,事实不是这样子,或者事实就是这样子?
熊定中律师:
其实事实就是这样的。我对于做管理是有情绪的,这个情绪在于我觉得这非常耽误我做好一个律师,所以我是很不耐烦的。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少见于律所创始人。我觉得我在非管理场合应该还是比较有耐心,至少我情绪上不反感。就是人在这个位置上,就不得不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但凡提到管理问题,我就会出现情绪不太好的状况,我觉得反正我也没有挣钱,有情绪就有情绪呗。
业务分管合伙人:
我目之所及,贵所在管理岗位的这帮人,好像没有人乐忠于做管理。每次开完合伙人会,合伙人都会收获很多负能量,对于管理合伙人来讲是一个消耗的状态。用爱发电难以为继,时间长了的话,管理团队的迭代以及后续补充力量,这个是首席应该考虑的问题吧。
熊定中律师:
我非常欢迎有更多的年轻律师加入到律所的管理团队,我觉得这是个磨炼。我情绪现在比较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早期还行,早期我没有那么不耐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收获还挺多的。
我们律师日常处理的所有业务工作都是确定性的,这个确定性指的是我们工作的评价标准,一个事情对还是不对,是确定的。但是比较有趣也折磨人的是管理动作是没有对错的。你很难得出一个管理上是对还是错的结论,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人说你的决定是不是对的。有的时候就是靠权限,为什么清律这么讲权限,因为如果大家都去讨论,那就一定会出现一个谁都说服不了谁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先定下来谁来做决定,这个决定有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对错,只要做了就往前做,其实都有结果。
我们清律没有合伙人专职做管理,每个合伙人都在同时做自己确定性的业务和不确定性的律所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极大的锻炼了我对不确定性事件的处理能力。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收获。所以我特别期待看到年轻的同事在这个钉板上滚一滚,感受一下这种不确定性。跟你的整个律师思维完全相反的不确定性以及你如何确信自己说的是对的,或者说如何在习惯认为自己是对的情况下,还要去尊重别人的意见,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挑战是管理岗最具有价值的地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你管理动作的错误会把其他人都坑了。做律师如果错了,责任是我自己,可能丢掉的是自己的客户,在律师行业里面有一个负面的声望。但是作为管理者,你的一个错误决策坑的是律所所有人。我们现在在管理合伙人会上依然有很多意见的交锋。我不知道包括你在内的其他管理者们是不是意识到了自己说出去的那句话如果被采纳了,但最后被结果证明是错的,你们会不会有心理压力,反正我的心理压力是挺大的。
业务分管合伙人:
对于干管理不挣钱的清律管理合伙人来讲,因为没有直接的风险,所以可能不太有这种决策上可能面临的压力,当然像首席这种自我要求比较高,道德感比较强的人,会给自己施加一个压力。我倒觉得在管理岗位上,大家受到的压力主要是与熊律直接沟通的情绪压力。
对于想加入到管理岗位的律师,我再说一个我的观点。熊律刚才说他目前的收获比较少了,但我认为目前阶段的管理合伙人收获其实是会比较大的。首先就是你会有一个不同的维度,你在一个机构的管理者的视角上看问题的方式跟你做律师的方式是天然的不一样的。不管你在这个岗位上干的好还是干的坏,首先你就多了一个维度。这个维度,从一个最功利的角度讲,就是你跟客户的沟通也好,还有你的业务的办理也好。其实你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客户,尤其是他的创始人/管理者,在一个同频的这个角度上交流,而不是让人觉得你就是一个做事的律师,他会跟你有更强的粘性信任感。另外一个就是跟熊律师的沟通的机会,这个本身是有价值的。
我跟他的沟通当中,也有两方面的收获。第一就是直接的提升。我们的主办律师包括助理,大家在为数不多的跟熊律师一起的会议或是其他的场景中应该有感知,就是对你的思维方式或者方法上会有一个提升的指引。
第二个就是负面情绪的承载能力。我跟我的助理开玩笑讲,就是什么时候你们能跟熊律师很愉快地聊天了,你们去面对法官的时候,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可能是我目前在律所管理岗位中比较直观的一些收获。
熊定中律师:
我感觉你搞了一个管理团队招新的宣讲,我觉得后续律所的管理还是更多的交给专职管理人员去处理。所以这种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少,因为岗位会越来越少。其他同事还有没有感兴趣或者想了解的?
S律师:
熊律是不是可以从首席的角度来讲讲有哪些事情是不符合清律的文化的。
熊定中律师:
比如大家看到的几个处罚决定,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写,在这个事件没有出现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会出现这种事情,但是在出现之后,我们就需要去审视,到底问题在哪?
我只能说从已经出现的事情里面能够统计出来的,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清律对外统一的形象是必须一致的。我相信大家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他在具体的一些场景里面,就会产生千奇百怪的理解。
我们说过的例子,你可能出于一个美学的考虑,改动了我们律所的一些制式模板,自己定制名片对外散发。如果你对于清律原来的做法和已经形成的东西是不认可的,你的做法显而易见不应该是自行其是,而是提出你的观点,然后争取更多人同意你的观点,然后去改掉。
甚至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有哪个主办律师觉得清律的管理结构不合理,不应当有一个首席合伙人,应当各自分管。那你的做法也不应当是对外去说,我们清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岗位,而是应该去发起这样的倡议,说我要通过合伙人决议,把这个岗位去掉,这才是我们清律一贯的风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直持开放态度。
早期的时候,我们合伙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很多,但是分歧归分歧决定了就执行。但是你不能够私下以另外一个标准去自行其是,这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几次处理的行为和事件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不是说故意,而是说无意或者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因为确实是出了事情,我才能够去处理事情。处理事情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不是个常识。可能因为我们不同背景,不同的文化,导致了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理解不一样。
业务分管合伙人:
现在管理团队的风格与当年还是区别比较大的。我的感受是现在的管理风格不像以往那样,没有了在管理信息上面更充分碰撞的这种场景。
熊定中律师:
郑律师作为一个优秀的律师,在这个环节陷入了迷茫,一个是对于自己分管事务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带领律务团队继续往前走。第二是陷入了对于管理侧管理风格的迷茫。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也是个新的挑战。
(在清律的第二个五年,我们需要面对管理侧人都不在一起的情况下。在具体办事上肯定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具体的一些执行上、沟通上,在情感方面的交流上,是不是有共识。)
C律师:
关于律所的行为模式问题,有2个问题想延伸一下。
第一个问题,您提到说我们所的一个议事流程、议事规范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所有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谈的,但是在没有明确之前是要遵守所里的规范的,如果说你对制度有一些不理解不满意,你应该去改变,去推动立法。这个推动立法的变革,可能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在这个规范不够明确不够清晰的情况之下,我们存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第二个问题,您提到说所里的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谈的。那假如说律所未来的架构、初衷还有制度,可能变得让您非常不满意的情况之下,您作为一个创始合伙人,现在的首席,那您会选择离开吗?
熊定中律师:
我特别喜欢C律师这些问题,我也特别期待我们清律的年轻一代都是这个风格。因为没有什么好顾忌的。我之所以不想理你们是不想理你们,并不意味着我心里就觉得我比你们高一等,我只是单纯的不想理人。这是一个大前提。
在清律改变一个东西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清律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清律能够迅速发展到现在,很多时候是模式的胜利,这个模式有个很重要的点是他真的是由大家来去决定事情。所以如果对于某个东西不满的话,大家一定要提,我们的章程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你们看一下议案的前置要件,真的一点都不难。我们清律从组建团队开始,每次开会真的是拿着章程在说话。表决的时候都是根据章程内容去算大家有多少投票权然后去投,而且决定之后所有人都会去服从这个决定。
这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初始的原则,就是保持对现状的积极不满和改进动力,所谓的积极不满,你不满你就提出来。
那对于你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点,就是你说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怎么办?这个在清律也非常的简单。清律是分管主义,我们都有对应的分管人员。你只要能够确定这个行为的性质,你就可以去问这个对应的分管人。请大家注意,章程里面写的很清楚,我们的分管对于分管事务的具体执行有决定权。如果你对于分管的决定不满,你可以找我,我也会复核他的决定是不是对的。如果你对我的意见再不满,你可以在凑到足够的人数后,发起合伙人会去推翻我的决定。
在清律,除了合伙人会之外,没有任何决定是不可以挑战的。而且我个人觉得我非常希望看到挑战。因为在这个挑战过程中,各方都能够进一步地加深对于律所的理解。当然关于所谓的强执行的问题,在挑战成功之前,一定要按原计划执行。
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要是哪天清律让我不满意了,我就不干了。这个可能性当然会有了。
目前我们的创始合伙人里面只有我和郑厚哲还在做管理,其他人都没有做了。
清律有一个很奇怪的初始的心态是没有人把清律当做自己的孩子,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几乎所有律所的创始人都觉得这是我自己养出来的孩子,我要控制他,我要让他按照我的意愿成长的。但从现在已经辞职的清律创始合伙人那来看,我觉得都不像有这个想法。我肯定是没有这个想法。清律是清律,我是我。之前有律师问我,我对于我团队的要求比对于清律主办的要求要高,我说当然,因为我的团队代表的是我的形象,但清律可不代表我,所以清律的律师在外面做了什么糟糕的事情,我并没有觉得那么丢人。我只是在我35岁到45岁,这十年内正好履行了清律首席合伙人的管理职务而已,没有别的任何其他的情感在。所以清律如果合适,如果依然符合我的要求,他依然对我有吸引力,那我当然会在这。如果没有那就不在这。我认为这是大家的平台,不是我自己的平台。这是我一个很基础的认知,从当年表决创立清律的那几个人里面,大家应该都是这个心态。
业务分管合伙人:
每个时期可能你对你的职业和个人的成长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一辈子还很长,不用把自己绑在一个地方。
C律师:
您和郑厚哲律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组织架构和这个组织成员之间架构更像是成员实现个人目标的一个载体,而不是说人为这个组织机构去服务。
熊定中律师:
我觉得我们都是被迫推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我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要做管理。但是既然你做了,你就得做好。我刚才说的,我说我心里压力很大的缘故,我觉得我做律师要做很好的律师,我做管理者也要做很好的管理者。
如果我的管理决策错误,导致了一个机构丧失了它本身应该发展的机会,或者是承担了其他的损失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很丢人,这不是道德感,这是对自己的要求。
对我来说,清律的首席就是一份工作,这个工作为期十年。我干完我就要干别的去,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我自己更自豪的是,我作为律师的身份,而不是作为管理者。
业务分管合伙人:
我的理解是,组织本身它是有生命力的。不一定是说有这几个人在这个组织才存在。每一代的人会有每一代跟这个组织的联系。清律在这个地方,就是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平台,能够让一些人有一个时空交集,在这个有趣的场景中,然后让一群有趣的人能够聚到一起。我觉得这个组织的意义就在这,不存在说某一个个体需要跟他有一个很强的联结。
· 加入清律的初心
· 律师在律所的行为边界是什么?
· 我们到底哪里不同?
市场分管合伙人:
熊律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有感触,他说“如果要让大家以‘为了清律’的名义而去做一些实际上大家都不太愿意做的事情,那清律这个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作为一个从业近20年的律师,因为每天都很忙,确实很难静下心来想一想,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们内心到底坚持的是什么?熊律的这句话也让我想起我加入清律的初心。
我们在清律这个平台上也遇到了很多事情,我举个例子,之前我们代理的艺人遭遇了一些网络暴力,在所有人对这个客户口诛笔伐的时候,我们当时坚持的是什么态度,这一点,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在清律这个平台上,大家的初心都是非常一致的。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会一起聚集起来,在清律的这个平台上体现出所谓的一种不同。
在这个行业时间长了,慢慢可能会变得世俗化了,反而会显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初心,他就变成一个不同了。这是我对我们会不同中“不同”的一个理解,今天也想以这个事件为起因跟熊律聊一聊。熊律作为我们清律的创始人,对于“我们会不同”这样的一句slogan是怎么样的一个解读,以及在熊律眼中我们清律要保持的一个不同是什么样的?这一点我们想请熊律再展开讲一讲。
熊定中律师:
这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念,因为我特别反感打着“为你好”的名义来给大家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要求大家不要做什么给其他人添麻烦。
清律不会管你想要做什么,但是有些事情明确是你不能做的。例如我们2个月一期的业务培训,我们也不允许利用部门命令大家强制参加。可能很多所都会说,你要提升律师的职业技能,你要做的更好,那你为什么不来呢,你必须来,这是为你好。但还是那个逻辑,为我好,但不见得是我要的。当然为律所好也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很多决策的一个基础点。
有很多的场合,我觉得我都在面临这种理念上的挑战。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创始合伙人之一金宏伟律师,他是做刑事案件的,他也做了很多敏感案件,当时他离开清律选择其他律所的理由,他也说的很明白,他希望可以办案更痛快一点,他当时的做事的风格必然会给律所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提出的这个理由,也引起了我当时的一个思考:如果他不走,我们会把他边缘化或者另类化么?我觉得不应该。律所应当支持或者说至少不应当反对律师选择做的合法的业务,即便这些业务可能会引起律所的风险。
如果你在这个事情上退缩了,那你的退缩就没有底线和边界了。我们的边界是法律的规定以及我们的执业规范,如果法律和执业规范都没有禁止律师代理这些案件,而只是律所出于商业考虑,去阻止某一些律师采取这样的从业行为,我觉得是不妥当的。当然,这也跟清律的非商业机构的定位有一定的关联,它是环环相扣的。
在这个事情上,我注意到,在最近我处理的一个行业内比较关注的事情时,对方提出要我们清律的成员在这个事情上保持缄默。而我的观点是,我绝不可能让我的律所做这样的一个承诺并对内要求同事保持沉默。律所为什么能干扰我的言论表达?虽然是律所的事情,但是你给我添麻烦了,我还不能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吗?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就是我觉得律所是律所,律师是律师,律师有权利按照自己生活的方式以及人格上的一些偏好来做出合法合规的事情,当然,你不能随意评价我们自己的客户,这是执业伦理的一部分。
清律只是作为一个冷静的支持者,一个支持平台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不能够取悦所有人,我们只能够取悦欣赏我们的人。而恰巧万幸的是,清律目前都还在一线或者说是准一线城市,在市场足够大的情况下,哪怕欣赏我们的人比较少,而且可能都还偏年轻化,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让我们无法立足。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说从时代的发展而言,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我们的人会更多。所以当时说那种话也不是故意说漂亮话,就是很自然地得出这个结论。
我们管理侧的同事们,真的也应该想想,就是这个观念如果落实到自己的管理动作上,也应该尽量少的以律所的名义来强制要求大家。除非你确信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以至于你得命令大家做,比如说我们就不允许年会请假,愿不愿意你都得来。那你说完全没有强制性吗?那就太一团散沙了,而且也影响我们的效率,但这个事一定要非常的小。如果你拿不准,那就先放着,先不要以清律的名义来强制。需要我们动用命令的手段来去做一些要求的事情,一定是我们笃定确信这一定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其他的你可以用游刃有余的一些管理手段来处理,例如有一些财务上的管理、人事的一些劝导。包括我们这几次这个业务分享虽然没有命令,但大家的参与度也都蛮高的。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以一个柔和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因为你用柔和的方式,好处是即便你错了,你也不用担责任。因为是大家认可你的理念,然后认可你这个观点,才跟你一起做事情的。如果有责任也是大家一起的责任。
市场分管合伙人:
我作为分管清律整体形象的市场分管合伙人,其实有的时候也在想,我们的主办律师在代理一些可能会给律所带来负面影响的比较有社会影响力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平衡?
我自己也同样经过这样的事情,我的客户在遇到一些引起社会影响力非常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第一时间提出说是不是需要为了律所的整体形象,选择去不代理这个案件了。但是实际上,我感受到了律所非常大的支持。我觉得清律所有合伙人的价值观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我们不惹事,但是我们也不怕事,对于应该坚持的原则和观点,只要是符合我们律师职业规范的,符合法律的,符合我们职业道德的,那我们就是支持的。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同行,在一些事件出来以后,可能管理层会说,你们不要去发评论,不要怎么样。但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了,一旦你为了一个所谓的“大局观”,然后要求大家去做一些妥协或者退让的时候,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因为他的这种管理的方式、思路和理念背离了作为律师本身应当坚持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自己其实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到底要做怎样的律师和怎样的律所。其实有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清律的合伙人们都还是有这个担当的,大家在价值观上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在某些我们应该去坚持的原则上,其实大家是共同去守住了我们的底线。我们清律现在体现出来的形象,就是我们清律不怕事,对于一些我们应该坚持的事情上面,我们还是很刚的。当然我作为主办律师我是觉得我得到了支持,但是对于整个清律的管理,其实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又要有担当,又要去维护清律整体的一个形象,那我们要怎么去平衡?也想听听熊律的看法。
熊定中律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但我要特别澄清一点,就是清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特定的态度。它既没有很刚,也没有怂,这个词在律所是不合适的。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但是清律到现在为止展现出来的刚,主要是因为我的个人风格,与律所关系不大。
关于律师业务可能会对律所带来负面影响而需要律所做评估的情况,我的问题是一致的。第一,是否合法;第二,是否违规。如果一个代理行为既不违法也不违规,那对于清律来说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们拒绝律师的业务是要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只能是法定或者行业规定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商业目的。这个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这也是清律的一个逻辑。
如果说基于商业角度来判断,认为这个会给律所带来更大的损失,会给其他的律师收入带来影响,那对不起,只要他是合法合规的,那你就得忍着。但这跟我们之前说的不要给其他人带来麻烦是不矛盾的,因为有些麻烦是因为客观,我们依法依规从事一个行为之后,他也有可能会带来麻烦。我们有很多律师都受益于其他同事的业务带来的荣誉,所以当然也有义务要承担其他律师合法合规的业务给你带来的不便。
我们一直强调,清律不是大家的家,我们就是一个依法合规来保障大家合法合规运行的一个机构。我跟朱律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她的一些行为我会以个人的名义来支持她,但是当我作为首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不带感情的判断者,在业务上判断是否合法是否合规。如果是一些道德行为上的负面事件,那清律也一定会做出公开处罚。
我们不先预设有什么后果,但一旦出现了来自外界或是主管机构的压力,且这个压力真的大到律所无法承担了,那我们可以再议。我们不会为了回避这种不恰当的压力而去让我们的律师先做让步。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中,没有朱律提到的那样有更多的感情,就是律所只是做了简单的是非题的判断。如果这个事情律所层面除了许可律师做之外自己还要去背书,那可以再行表决。
我作为清律的主办律师,我申请在律所的平台上发言,你表决的是允不允许我发言,而不是认不认可我的这个发言,这是两件事。律所的观点只是评判律师的权利是否被限制,仅此而已。这个点确实有点反常识,可能主办感受到的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基本操作。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错误,就进行公开处刑。所以从我的定义来看,清律真的是一个“莫得感情”的机构。
市场分管合伙人:
律师事务所其实还是一个人和性很高的机构,虽然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它会是一种没有感情的处理方式,但是这个所谓的有感情还是没有感情,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是取决于大家价值上的认同感。
我作为一个执业了近20年的律师,在清律这个平台上确实感受到了很大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到很孤独,虽然我现在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但是其实有很长的时间,我还是自己独立执业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想去坚持,但是你也会胆怯、会害怕会觉得我会面临不知道一个怎么样的境地,当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也会担心是否会给其他人带来所谓的麻烦或者引起大家的反对。所以当我感受到大家对于一件事情的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是非常得到支持的。可能这种支持对于熊律来说,就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题,但恰恰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够证明当我们在每一个需要抉择的关口,大家其实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去做选择的,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体现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别人认为我们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做了我们自己认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基于同样的价值判断做了同样的选择,并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的时候,可能别人就会看到说,你们这个机构好像是跟别人不同的。虽然我们在合伙人会上经常也会因为一些小事讨论的非常激烈,但是在这一些大局观的事件上,我们基本是达到了统一的,这一点让我觉得是比较幸运的。
熊定中律师:
我觉得朱律师也帮我理清了一下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我当然能感受到,你可能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支持。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很多大的机构他们的判断都掺杂了太多的是非规则性因素,导致这个市面上大家都没有做对的事情。有一个机构他就只是在做一个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大家就觉得好珍贵,好温暖。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本分,就是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有人提出我们说“我们会不同”,会不会是故意标新立异,你要“不同”在哪里?我们的角度是,得看我们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果没有面临这种业务的挑战,那我也不会去想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在很多地方其实都会体现他的不同,比如我们的年会。我们觉得律师应该凭本事吃饭,在我们官方组织的一个活动里面,你通过你的才艺获得更多的关注可能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我认为这不是在官方场合应当出现的一件事情。我们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因为某一些不纯粹的事情去影响我们的判断。当然我们还是有跟别人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合伙人的业绩也有一定要求了,虽然我们的表现形式一样,但是我们的目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目的是让更有精力,更有余暇去看整个行业,看整个律所的那些人,来承担真正的表决票,而不是在律所里去区分三六九等。所以在清律大家也不会去在意谁是权益合伙人谁是非权益合伙人,他只会体现在表决的问题上,即挣钱多的人有表决资格,仅此而已。我们不是非要处处跟别人不同,而是尽量把我们觉得那些本来就应该做而行业里面没有做到的事情做好。
当然可能限于资源,限于能力,限于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没办法做成那样子。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阶段性的工作,只要我们记得我们最早一起走到这个平台的时候,是想去改变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理的行业现状。只要一直记住这个初心,我觉得随着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员、更多的筹码,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市场分管合伙人:
我非常赞同熊律刚才所讲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律所,在很多的方面,我们也在成长和摸索的过程当中,我实际上是19年决定加入清律的,大概在这两三年的过程中,我个人也获得了很大的成长,特别是在承担了一些律所的管理工作之后,特别是在一些事情的思考角度上面,与原来仅仅只是做执业律所来说,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我觉得非常幸运能在这个平台上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一个三观,能够一起去保持这样一份所谓的天真及初心。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初心不变,那我们的这种不同,我相信是可以一直坚持下去的。



 2023-01-12
2023-01-12.png) 清律
清律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