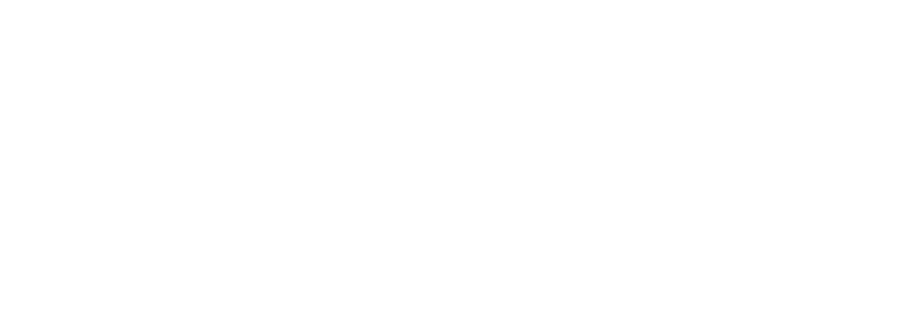· 当前律师行业转型现象是否普遍,其背后原因是什么?
· 年轻律师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应如何定位自己?
· 律师如何面对案源不稳定的挑战?
· 年轻律师如何克服独立执业中的焦虑和挑战?
· 清律如何看待律师个人成长和业务发展的关系?
Z律师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10日,清律『一言』的第七期,今天这一期的缘起,是某天我向首席提出了我个人的困惑:我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红圈所或者是大团队的成员出来独立,因为非诉市场不大景气而且又比较拼资源,诉讼相对比较接地气好接单,所以很多律师纷纷转向诉讼。不知道首席是怎么看的?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来诉讼的目标客户是不是会越来越下沉?像我这种没有太多资源和人脉关系的律师,是不是还是得通过熟人拓客再加上自媒体去破圈来维持创收呢?
熊定中律师
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因为清律这一年多以来有非常多想转做诉讼的律师加入,不光是红圈所的律师甚至还包括企业的非诉讼法务。在大家的传统印象中非诉业务一直是高大上的业务,我记得在我们深圳办公室刚成立的时候,我去深圳跟一些深圳的校友交流,有一位师兄还讲了很多关于IPO是律师业务的明珠之类的观点。当然,我理解它确实可能是一个可以给别的业务引流并产生案源的业务。
但是这几年来看,首先资本市场的不景气,整个投资活跃度的下降导致了越来越多(不光是红圈所)的非诉业务受到了冲击,你说红圈所非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原来这些大的、有利润的、高大上的非诉业务,实际上多数都被一线所承接了。所以真正受到冲击最大的反而是原来靠这些业务挣到了非常多业绩的团队或者律所。这个局势来临之后,肯定对高年级律师有一定影响。所以几乎所有做非诉出来的律师都说自己想做诉讼,想补全一下诉讼经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领域确实门槛要低一些,因为它有小案子也可以让你去做,但非诉基本没有小项目。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们可能要离婚、家里有老人去世、可能有继承纠纷、邻里纠纷或者随便做个小买卖就可能会有纠纷等等。纠纷一定是持续大量存在的,而且在大家法律意识越来越健全的情况下,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都觉得说需要找一些专业的律师,他们是认可专业性的。这个情况下就导致了诉讼的基本盘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高利润诉讼案件是在下降的。因为客户的支付能力在下降,但是诉讼的业务量随着经济的不景气还有可能会增加。
Z律师
如果说诉讼业务本身它就是一个存量市场。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又有一些以前原本不是做诉讼的律师,他又要转进来。那么原有的诉讼律师是否会产生焦虑呢?
熊定中律师
你来问这个问题很奇怪,我觉得应该是做非诉的同事们焦虑,如果他们想在这个领域里获得基本的收入保障,要怎么竞争得过像你这样一直在诉讼领域深耕的律师?因为很简单的一点,诉讼和非诉的思路差异还是挺大的。甚至说如果没有人带,你可能去看一大堆法条也能看懂,但是例如法院几点开门,法官几点能接电话等等,你都不知道。而这些事情当事人一问你可能就会露怯,这都不是书面知识。对于一直做诉讼的律师来说的话,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要注意的一点是,它会导致在这个圈子里面竞争变激烈。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是这个时代必然会带来的变化,它影响着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像我现在虽然也算是在争议解决领域做到头部的团队和律师,但我们的竞争也变强了,我们的报价金额也在下降。这种情况下,我的观点是,如果是一个时代的变化的话,你就不用去管它,只要大家都适应它就好了。你只要考虑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所以说如果你是代表非诉律师的同事去问的话,那我觉得让非诉的同事跟我对谈的时候去聊他们的困境好了。真正能够独立去完成自己基本生存保障的费用的获取,这个困难度更多的是非诉律师,你很难想象他们的困难在哪。
Z律师
我就替所有的非诉和诉讼律师问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现在市场环境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作为相对年轻的律师,可能比我更年轻,或者像我一样独立了三四年的这样一位律师,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之前问过您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样没有资源也没有太多的人脉关系,因为我本身是不太社交的人,我的社交领域是很受限的。然后您当时问我:为什么我会觉得没有资源?我当时回答的是我觉得稳定的才是资源,就是你的关系、人脉、交际圈子都是相对稳定的,它能够供给你案源,可以陆续给你输出,让你能够维持存活,我觉得这种才是资源。
熊定中律师
我当时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也很焦虑,我希望我有稳定的收入。如果我作为一位做争议解决的独立律师,我不能指望我身边的人,或者我影响力能够覆盖到的人,他们没事就有官司冒出来,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诉讼是偶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非常看重我的常年法律顾问。实际上对于诉讼律师来说,常年法律顾问是维持你内心稳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锚。这是我年轻时候的想法,但我现在觉得你们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我当时是负资产去独立执业的,没有完成任何的累积。但是咱们所做非诉的同事们,每次来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第一年你们的收入下降,你们扛得住吗?每个人都很乐观,跟我说没问题。所以内心的焦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至少有饭吃有地儿住。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如果我挣不到钱,我连房租都付不起。所以我的焦虑感来源于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常年法律顾问来保障我每年有固定的费用来负担我的房租、我的饭钱。但是坦率讲到这个时代,你们还需要一年10万块钱的常法来保证内心的稳定吗?你们自己没有这10万块钱,或者说你缺这10万你就活不下去吗?你们真的缺钱吃饭吗?不至于。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稳定性的需求只是来源于你们内心的一个弱点。如果没有生存危机的话,就真的只是一个内心的忧虑。
那么话又说回来,对于Z律师来说,如果没有常法怎么办?可能你们能从很多清律的决策中看出来,我的很多判断其实是相对比较宏观的,就像我当年认为远程办公,对办公室成本的压缩是大势所趋,我们现在依旧还在享受这个红利。那么对于个人来说,我刚才说了,我们不能指望我们认识的人每天都打官司,但是社会的诉讼率是相对固定的。如果说100个人中大约有1到2个诉讼是一定会出现的,这是个概率问题。那么对于诉讼而言,本来应该平滑运行的某一套体系、人际关系和商业交往如果出现问题,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在诉讼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假如为1%,如果你认识20个人,而这20个人都明确表示他们只信任你这一位律师,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平均5年才能赶上一个案件,那我为了让自己活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这次去深圳给客户公司培训的时候,也跟某个同事聊起过这个话题,她的第一反应是,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提高概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想法,你怎么可能提高社会的诉讼概率?如果你去提高你身边人的诉讼概率,那就意味着卖棺材的人到处去当街伤人,这不现实,不可能。所以,另一个角度是:扩大的社交面、扩大触达率。这个方法就是你要有配套团队,你要有买量成本,你是一个运营行为。如果把运营行为单独来看,你其实扩大触达率的方式就是多社交,多认识人。当然这个虽然是值得鼓励去做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收益率最高的做法。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回去可以想想,因为我当年刚独立执业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在想,我到底认识多少(能给我产生业务)的人?我当时数完这个的时候,我的心就凉了。因为我觉得社会的诉讼率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那我要保证我今年有案子做,我应该怎么办?我也有过你们现在的想法,那就是我要去多认识人,我也去做了这个事情。但我后来发现,我的社交圈是有限的,我能“认识”的人也是有限的。这里“认识”的人不是说我去参加会议,见一个大佬,这个人就是我认识的,不是,这个人不会给你带来业务。有同事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我去参加了很多活动,很多校友会,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转化。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参加的所有的活动里面人数少于四个的有多少?什么意思?在一个大型场合里面的这种泛泛见面,除非你本身就是那个聚光灯下的人,否则这不会是你的案源。就只是混个脸熟,我不是说没有必要,但是你不要指望会有转化。她说有一半,我说那很好。第二个问题是,你所有社交圈子里面,四个人以下的局里面,出现一个35岁到50岁之间的人,这个数量有多少?她想了想说零。我说那没有转化的结果不是很合理么?
为什么要说这个年龄段?因为大量的社会资源是掌握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手里。你想想看,你所有接触的公司里面能够决定一个案子给谁的人是什么年纪?35以下吗?绝对不是。所以就意味着你没有到那个年龄段,你没有跟这个年龄段的人打交道。你想想看,当我30岁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混一个50岁的人的局呢?他们会觉得你就是个小孩。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种社交就完不成转化。当然,这是一个储备,可能未来也许会有。我们所里参与社交圈和自己年龄差最大的可能就是L律师,L律师之前跟我沟通时,困惑的点就是为什么这些人里面没有案子给我?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只是你的年龄还没有到去分这个社会的主要蛋糕的时候。你等就好了,那除了等还能做什么呢?总不等自己慢慢变老?当然不是,我当时的判断是,那我要让这二十个人能够对我的信任程度达到,他们愿意把他们认识的人介绍给我。就是我不去加强广度,我去加强这二十个人的深度,通过我的努力、认真,把他们所有交办和求助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办理,让他们对我极度认可,让他们认为说:这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靠谱的律师,我愿意把他作为一个你都不太能够碰得到的好医生介绍给我的朋友。那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把我介绍给他们朋友,不是给我面子,而是在帮朋友忙。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社交圈子跟我不一样,他们每个人假定也有20个关系好的朋友的话,这意味着我的影响力是400个人,而不是20。回到我们之前的判断,如果这个社会的诉讼率是1%的话,意味着我每年至少有4个案子。这个逻辑合理吗?这十几年下来是验证过的,我早期的大客户都是这么来的。我的第一个上市公司的客户是我原来的小常法客户,当时跟客户关系非常好。在上市公司收购他们的时候,就把我介绍给他们集团。老板们会有自己的圈子,只要你把事办好了,他甚至都会觉得你能办好他那些朋友的案子比给他钱更宝贵,相当于他帮人解决了一个问题。所以这才是一个正统的律师的案件来源。在商业运营的部分,你的案子就只是挣钱,这一单做完就完了。可能在一万个观看人里面,有1000个咨询,然后转化200个,这200个可能做完就完了,从此陌路了。你就要不停地去做陌生客户,当然这是运营模式。而真正跟着你一起成长的客户才是我刚才说的,怎么把自己的现有客户做深,还是取决于你真的要把他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办理,然后可能还需要看运气。
Z律师
我那天问熊律的时候,其实熊律跟我说了一句金句,当时听了感觉豁然开朗。其实我的点是我的案源来源没有那么稳定,一方面取决于案源方的个人偏好,还有就是公司运营,因为我去年有一个常法,但是今年公司黄了,所以在我案源来源没有那么稳定的情况下,该怎么去面对?
熊律当时说了一句话:稳定的只有你的个人品牌,而不是你的客户。你外化的稳定的只可能是你的品牌。我也想把我的想法分享给所内的其他律师,像熊律刚才说的,不只是原有客户的深耕,你原有的朋友,你原有认识的人的深度的挖掘,以及你每一次合作的所里的合作律师,包括你的老板都是你非常宝贵的未来可能的案源来源。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的深刻体会。我作为一个案源提供方的时候,你处理事情的精彩程度、靠谱程度会决定下一次我还愿不愿意再给你介绍案子。那反过来我这么一想,给我介绍案子的合作律师,他也一定希望看到我能把他给我的案子处理好,你这么换位一想:当你自己是一个卖方的时候,你就想作为买方的时候,你的偏好是什么,这个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那天我还问了熊律一个问题,如果我花了很多心思维系的这些人,不管是公司的客户也好,当事人也好,合作律师也好,他们的运气没那么好,他们混得都很一般,可能还面临着随着市场的竞争激烈,慢慢萎缩。那怎么办?是不是意味着我的业务也就这样了?
熊定中律师
说实话就是如果严格定义的话,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比我的客户发展得更快。在这个过程中,你说怎么完成这样的一个跃升呢?我觉得当你累积到一定的影响力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在我们某一次会上,分享不同阶段的律师需要具备的能力,你如果想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跃升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一定要破圈,破圈的方法有很多种,有可能就是一个关键的人或者关键的企业;也有可能是在做很多的对外宣讲和宣传中偶然收获的一个机会,你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说实话有点玄,第一你要有运气,第二你还要在运气来的时候,抓住它。举个例子,我自己在早期做互联网领域的时候一直做的是互联网广告的公司,其实和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没什么关系。但是第一次变化就发生在Z老师介绍我去参加某公司的闭门会。这个闭门会真的是个闭门会,就是一个内部的闭门学习活动,没有任何收益。我当时只是觉得挺有趣的,我觉得跟这些老师们一起闭门学习四五天好像也挺好的。在参加的过程中我展现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这个活动就是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正好有机会向一起参与活动的互联网公司展示我自己。让参会的互联网公司的骨干们认为“这个律师好像还挺专业的”。至于我为什么能被邀请进去,除了Z老师推荐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在前一年广告法出来的时候,我跟某个公司合作做了一个分享讲座。在分享讲座的三四个月之后,某个行业头部企业的一个法务说有一个广告法的案子想找我,因为听了那个讲座。我在做讲座的时候也并没有预想到有这个结果。当我做了他们公司的业务之后,就进入了科技领域。当你办这些案子,当你给他做支持的时候。你同时也开始从他那里学习,他有很多的合规策略、合规要求、合规需求其实是很多公司过了好多年才有可能遇到的,也就是说当你服务一个头部企业的时候,你已经占了这个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个头部,就是这些关键节点让你完成了这些跳跃。后面我开始做反不正当竞争的案子,说实话当时这些案子的技术难度很低,但是大概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有一些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说的商业模式的竞争案件去找到你。所以我觉得你看,总会有一些关键节点让你完成跃升和转化。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一定会碰到他们。坦率讲,早期的时候我也没有预期,如果没有这些节点,或者说我没有准备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觉得我脾气不好的,没有觉得我专业不行的,或者说在案件的尽职程度上不够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可能也有很重要的实力因素。
Z律师
熊律在所内的公开分享,他确实是用他个人经历很诚恳地在跟大家分享这些节点。但是我跟他私聊的时候,他当时说得很直接。我说如果这些人混得很一般怎么办?熊律说,那不是说明你没有这个命,或者说你认识的人不够多,如果你做的业务足够多,总有人会出头。这个是概率问题。但是最后说的这句话确实也很一针见血,他说,与其担心这个,不如担心这些人混好了以后,结果他们最信赖的律师不是你。
熊定中律师
你认识那么多人都混不好的概率,我觉得要远远低于你自己混不好,他们换律师的概率。我那么多客户是怎么来的,那就是他们把原来的律师换掉换成我,那那些律师不就成了炮灰了,谁会关心他们的郁闷呢?说被人把客户抢走了。
Z律师
我总结了三点,第一,继续要打造个人品牌,让跟你打交道的人,不管是所内还是所外的合作律师、曾经带过你的老板、你的师父、你的客户、你的当事人,你现在服务的这些人,让他们有更明确的感知你很专业;第二,扩大业务和人的分母提高概率;第三,做好前两点,把一切交给时运。
熊定中律师
我一定要打断你的这个表述,我觉得对于我们所的绝大部分年轻律师来说,你在谈专业知识的时候,先谈靠谱。谁才能够评判一个律师的专业?是高级别法务,而你们能在一个新的领域碰到高级别法务吗?你们可能碰不到,你们碰到的很多是创业公司的老板,他们不是学法律的,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专业?根本不知道。绝大部分客户对专业是没有评价能力的,除非你服务头部企业,你跟不同的顶级律所竞争,由他们的法务来评判你是否专业。你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靠专业拿到案源。你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那没有到那个时候靠什么拿案源呢?靠你的靠谱。什么叫靠谱呢?客户谈了之后,什么时候反馈,什么时候给方案,沟通的过程中是不是时时刻刻替别人着想,提醒别人,有很多东西他感知不到专业,但是他能感知得到你是不是尽心,尽心就能够让你在成为一个大律师之前,获得足够的认可度。你都不需要专业,还没到拼专业的时候,你的报价是不是靠谱,你跟客户的沟通是不是顺畅,你是不是真的为他着想,这个人家是能感受得出来的。在中年级以下或者中等地位的独立执业律师的这个圈层里面,靠谱要远远高于专业。而且说得不好听一点是你不专业,这个事情就办不好了吗?举个例子,我有一年出差,正好跟某位曾经做过我助理的律师约了个饭,她就习惯性地跟我讲她办了一个案子,我一听我就说你这个方案不专业,我马上给了她一个我觉得这个案子更合适的方案,她一听觉得也对。但是我后来仔细想,她的方案能办完这个案子吗?我觉得可以,无非就是磕磕绊绊一点。就类似于说你从A地到B地一定要开跑车吗?不一定,你开个破车也能去,无非就是慢一点,但人家也就付了个慢车的钱,也不指望你用跑车跑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启发我,其实有的时候在专业上追求最优解,所谓的工匠精神,所谓的精益求精,我觉得只是一个虚幻的律师们的自嗨。我现在看到那种宣传,说我打磨我的起诉状,打磨好几天。我都觉得好笑,你是什么案子,值得一个起诉状,打磨好几天,字斟句酌,一个字一个字的改,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陶醉的行为,没必要。你只要踏踏实实地、认真地把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做,客户能够感受到这种态度,就够了。
Z律师
其实在我独立到现在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里,前面那两年多,我一直觉得比较混沌。我是很依赖于身边要有合作的律师,两个人一起出去谈客户,一起去面对庭审的一些可能的问题。但是我发现最近这半年多,虽然可能焦虑,但是我这半年多确实是成长最快的。
熊定中律师
你焦虑的点是什么呢?
Z律师
焦虑的点,就是说我自己在面临一些比如说客户可能的苛责,或者说开庭的时候,那些突发情况,如果是自己的话,我也可以处理。但是我会觉得心里的包袱,心理压力会非常大。原来做助理的时候可以与合伙人商量,现在的点就是没有人可以商量。
熊定中律师
我坦率讲,清律在23年之前,对于年轻律师都非常不容易。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机会商量,就是你们是陷入了一个单兵作战的状态。但这个历史的缘由来源于我们早期这批合伙人跟你们年龄代差几乎有十岁。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不愿意跟他们聊,他们是不是自己在聊,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跟他们聊。然后人又少,尤其是清律北京,早期的话,就是自己搞自己的事情,没人管。等你们这些新进的90左右的律师来了之后,开始出现一个情况,是你们要找我们聊。说实话对于你们来说,要就一个具体案件怎么办理去问我,估计你们难以克服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那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有一个人商量,不一定非说要获得某个建议。我只是说我有想法,我说出来,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然后你能给我一个反馈,无论是说好还是不好都行,反正我说出来就有个交流,对吧?去年突然来了这么多年轻主办的律师,我觉得是开始改变的契机,我当时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我说要力推一下,成立青联会之类的。我理解我不能解决老合伙人,尤其是我自己的性格问题,我也不想那么为难自己。但是我觉得既然年轻人都来了,那么给你们渠道,给你们平台,给你们资源,包括资金的支持,你们自己去做,我觉得就可以了。还是那个逻辑,就是我觉得我不想干这件事,并不意味我觉得这件事是不对的,只是因为我不想干,而且我觉得清律也可以不干,但是我给这个平台让大家自己去聊。我是特别乐于看到你们自发的去组织,然后形成小的团体,去沟通你们的生活和执业上的各种困难和困扰。这是我非常乐意看到的,但是我不会去组织,因为我不确定谁会不喜欢。我觉得就是一旦我去参与或者管理层去参与一个行为,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变得很重,意味着变得大家可能不参与就不合适,我觉得有可能会违背一些人的意愿。所以我宁可说你们自己去玩去吧,反正清律提供这个平台和机会。我觉得至少对于现在的清律而言的话,这个问题,如果你自己不是完全被动的等着别人安排的话,其实你们现在是有交流的地方、交流的人群的。因为年龄层,包括背景都差不多,大家可以一起去聊一些你们想要的。
Z律师
我自己的感触是,我是在清律完成了整个开智的过程。不是说我现在智慧到什么层面了,只是相对我之前的认知而言,清律这个平台就是因为他给的自由度,包括没有那么多交流,没有那么多说大家一起讨论案子的这个情况,反而逼着我自己更独立,然后心智也更成熟,也更自由。但是我确实也觉得,像之前我们在团队的那种氛围,比如说团队同事好像更像战友,大家一起频繁出差,同吃同住,可能还顺道转一转当地的景点。大家的这种人际关系很紧密,包括现在离职了以后,我们也会定期地吃饭,交流新的想法。我那天跟熊律说,其实这种交流会让我觉得有获得感。熊律当时问我说,你要搞清楚到底是获得还是获得感。然后我想了想我的答案,我今天也可以分享给各位,我的答案是,是不同的人大家聚在这儿分享了不同的眼界,不同的见识,我觉得这是一种获得。但是你坐在这儿交流输出你的观点,以及跟其他同事观点碰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获得感,这对我而言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虽然平时在家远程办公,但是其实有这个场景,场遇,大家有机会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多主动找一找同事多交流,反正至少我自己现在也是有几个固定的同事,没事聊一聊最近的状态,然后我调整的还挺好的。
熊定中律师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分类特别好,到底是要获得还是要获得感,我为什么不愿意跟大家交流?因为我觉得跟你们交流,我没有获得。我跟你们交流,我还不如跟AI聊天,我获得更多。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需要的是获得感,就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价值。我尊重大家愿意为了获得感去多交流,但是搞清楚一点,如果大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自己的情绪价值,为了要获得感的话,那么就可以更加的开放一点。就不要局限于任何跟知识点或者说业务相关的事情。你们觉得你们希望跟你们的同事分享你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就去聊吧。



 2025-01-02
2025-01-02.png) 清律
清律
 上一篇
上一篇
.png)